古蘭經的第二次正典化(324/936),伊本•穆傑希德和七種誦讀法的創立
作者:沙迪•納塞爾(Shady Nasser)
在《古蘭經的第二次正典化》中,納塞爾研究古蘭經文本和古蘭經誦讀法的傳播以及人們的接受情況,誦讀法有各種不同版本,該研究參考了伊本•穆傑希德(Ibn Mujāhid)(卒於324/936)所創立的七大以誦讀者命名的古蘭經誦讀法系統。這個包羅萬象的項目旨在追蹤和研究古蘭經所經歷過的細緻的修訂版本,在1,400年的歷程中,從背誦口述的形式開始,最終形成一個靜態的、系統化的文本。
有史以來第一次,這本書提供了一個完整和詳細的文檔,包含伊本•穆傑希德記錄的古蘭經的所有不同變體的誦讀法。隨書附帶一個全面詳細的音訊記錄,其中有3,500多份不同誦讀的古蘭經誦讀音訊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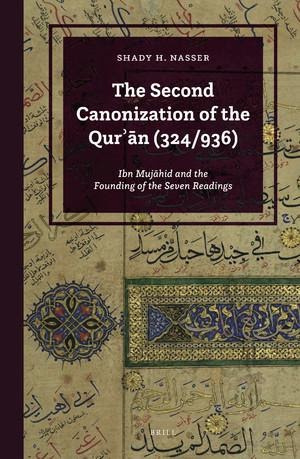
內容目錄
致謝
前言
第一章:正文前書頁。古蘭經的第二次正典化
第二章:適者生存
2.1:公認誦讀法的不規則讀法
2.2:伊本•穆傑希德的《薩布阿之書》(Kitāb al-Sabʿa)中66個有問題的傳述
第三章:聖訓和古蘭經的里賈爾(rijāl)考證
第四章:重新審視口述表達。誦經學(Qirāʾāt)的書面傳述
4.1:區域性的法典
4.2:早期不同形式的誦經學傳述
第五章:古蘭經變體的本質
5.1:通過誦讀古蘭經的原則(uṣūl al-Qirāʾa)使阿拉伯語和古蘭經文本標準化
5.2:古蘭經的個別的變異(farsh)
結論與未來研究
參考書目
這部分翻譯自在線文章「The Second Canonization of the Qurʾān (324/936), Ibn Mujāhid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Seven Readings」
https://brill.com/view/title/55138
--------------------------------------
結論與未來研究
我相信我在這本書中提出的資料以及我仔細研究的古蘭經的許多變體的誦讀法例子會顯示,七大以誦讀者命名的誦讀法是後來被構造,系統化並且封為正典,成為我們今天所知道的形式,遠在它們被假定的起源之後。此外,今天通過兩個正典傳述者(Rāwīs)再現這些同名誦讀法歪曲了這些正典誦讀法的傳述歷史。不幸的是,在伊斯蘭學者圈中我們仍然能聽到有聲音爭論說「哈夫斯(Hafs)從他的老師阿綏姆(Asim) 繼承的誦讀法實際上是阿里•伊本•阿比•塔利卜(Alī ibn Abī Ṭālib)從先知默罕默德那裡繼承的原件(master Copy)。」
同名誦讀法不是靜態的背誦系統,並非在歷史上某一時期創作寫成然後逐字逐句地代代相傳。它們經過了修訂、編輯、潤色和嚴格的內部系統化,才達到了現在的狀態。說到哈夫斯和阿綏姆誦讀法(或任何其他同名誦讀法)作為一個統一的背誦系統—在它們的背誦原則和個別變異中—由一人之手獨立創造,是歷史謬誤,正如在書中的研究所展示的那樣。本研究的主要目標之一,以及我未來對古蘭經其他正典過程的研究,是要克服說文本是靜態的這個誤解,並證明古蘭經作為一種口述完成執行的文本,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演變和發展。
我認為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古蘭經本身的概念,它的性質,發展,以及古蘭經被接納的歷史。若假設第二/第八世紀早期的穆斯林完全熟悉整個古蘭經文本的細節詳情,這樣的假設是可疑的。在伊本•穆傑希德所著《薩布阿之書》中的同名誦讀法的文獻記載顯示,這些系統化的誦讀法處於發展過程中。我們在這些系統中發現的矛盾差異和變化改動之處,指出了一個誦經學學術方面格式化的時期,那時的穆斯林正集合眾人之力試圖有組織地將抄本(mushaf)所執行的情形封為正典。在第一章中,我提出了一種新的年代學,關於古蘭經所執行的文本歷史中的關鍵階段,也就是誦經學。第一次正典化的發生,源於奧斯曼(ʿUthmān)將抄本編纂成冊,還有早期語法學家努力研究阿哈邁德•瓦基勒(Ahmed El-Wakil)的著作,《對古蘭經的收集和可靠性的新看法:「原件」存在性的情況以及這與哈夫斯•本•蘇萊曼(Hafs ben Sulaiman)從阿綏姆•伊本•阿比•努迦得(Āṣim ibn Abī al-Nujūd)繼承的誦讀法有什麼關係》(New Light on the Collection and Authenticity of the Qurʾan: The Case for the Existence of a “Master Copy” and how it Relates to the Reading of Ḥafṣ ibn Sulaymān from ʿĀṣim ibn Abī al-Nujūd),《什葉派伊斯蘭研究期刊》8:4(2015):409.258,使阿拉伯語(al-ʿarabiyya)標準化。
第二次正典化發生於伊本•穆傑希德之手,他寫了《薩布阿之書》,而第三次正典化發生於丹尼(al-Dānī)和沙提筆(al-Shāṭibī)之手,他們創造和推廣雙傳述人正典。伊本•加扎利(Ibn al-Jazarī)是第四次正典化背後的主導力量,他以「半官方」的方式將另外三個同名誦讀法整合到一起,並且通過正典之道(Canonical Ṭarīq)(複數Turuq)進一步系統化誦經學的傳述。第五次正典化的過程發生於20世紀,愛資哈爾(al-Azhar)首次印刷出版了使用哈夫斯和阿綏姆誦讀法的古蘭經。在第二章,我深入查考了shawādhdh al-sabʿa的概念,正典誦讀法的不規則誦讀,並且研究了伊本•穆傑希德所著《薩布阿之書》中的66個傳述錯誤。
我的結論是,同名誦讀法並不是作為一個單一的、統一的系統編寫創作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同名誦讀法中的差異和變化都被剔除了。
我認為將同名誦讀法正典中的某些傳述人排除在外,背後有不同的原因,並提出地理關係,專門化的主題,堅持同名誦讀法的學生達成一致,這些在正典化的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第三章中,我比較了誦經學和聖訓的傳述機制,並且予以演示,由於兩學科原則上的完全不同的性質,將聖訓的方法論應用於誦經學在實踐領域造成了張力和混亂,特別是在有關正直(ʿadāla),可靠的傳述世系(isnād)的標準,以及聖訓傳述環境的事情上。
在第四章,我在誦經學的學科的框架下再度審視了口述和書面傳述的觀念,這種觀念是,誦經學的傳統在很早的初始階段就極度依賴於書面傳述的方式。誦經學學者彼此通過信件進行通信交流,掌握個人筆記和法典,他們以此來證明古蘭經變體版本並將之確認。除此以外,在庫法(Kūfa)、巴士拉(Baṣra)、大馬士革(Damascus)、麥地那(Madīna)和麥加(Makka)等地的法典中有阿布•烏拜達(Abū ʿUbayd)和伊本•阿比•達五德•錫斯坦(Ibn Abī Dāwūd al-Sijistānī)早期記錄的文本變體,在比較了他們的記載和伊本•穆傑希德《薩布阿之書》中的文本變體之後,我認為,五個主要地區的法典的信念(Imāms),在某種程度上與我提供的關於伊本•穆傑希德記錄的文本變體的資料相矛盾。我認為,那時幾個不同的法典在同時通行,並且,這些法典不約而同地在同樣的地理區域內被誦經家(Qurrā)採納查閱。
在最後一章,我在伊本•穆傑希德的《薩布阿之書》的基礎上,詳細地記錄了七大同名誦讀法的背誦原則和個別變體。背誦原則中極大的變化表明了一個誦經學的學術的形成期,在此期間誦經家試圖將古蘭經的口述呈現方式標準化。此外,個別變體的變體類型(farsh)的一般統計分析顯示出很高比例的類別與內母音,長母音,大小寫結尾,不完全首碼變化,和動詞形式差異相關,暗示著這些變體是密切與語法和形態不穩定相關聯,以及對古蘭經措辭不太嚴格的把控。除了需要對古蘭經其他正典化時期進行研究之外,還需要對這些變體誦讀法的語法,形態和語義進行更深入的分析。我在這本書中提供的資料庫將成為關於古蘭經變體誦讀法的百科全書的起點,該網站目前正在建設中,其目標是提供全面的古蘭經變體資料庫,借助誦經學,經注(tafsir)著作,古蘭經手稿和語法編譯。這將邁出新的一步,更好理解過去1,400年中古蘭經文本緩慢的發展和演化。
這部分翻譯自在線文章「Conclusion and Future Research」
https://brill.com/view/book/9789004412903/BP000013.xml
--------------------------------------
沙迪•H•納塞爾(Shady H. Nasser)
近東語言和文明副教授

沙迪•H•納塞爾
納塞爾教授,教授阿拉伯文學和伊斯蘭文明課程。他以前的職位是在劍橋大學(英國)亞洲和中東研究學院擔任古典阿拉伯語研究的大學講師。
沙迪在沃夫哈特•海因里希斯(Wolfhart Heinrichs)的指導下在哈佛大學攻讀阿拉伯語和伊斯蘭研究的博士學位。他於2011年獲得博士學位。2009—2012年,他擔任耶魯大學阿拉伯語高級講師和阿拉伯語專案協調員。2013年,他被任命為劍橋大學(英國)古典阿拉伯語研究大學講師。
納塞爾的研究興趣是一般的古蘭經研究,特別關注古蘭經文本、語言的傳述歷史,以及早期穆斯林社群對古蘭經的接受。前伊斯蘭時期和早期伊斯蘭詩歌,阿克巴(Akhbār)文學,和聖訓傳述也屬於納塞爾的研究興趣。他發表的著作包括:
-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Variant Readings of the Qur’ān: The problem of tawātur and the emergence of shawādhdh, (Leiden: Brill, 2012)
-
‘(Q. 12:2) We have sent it down as an Arabic Qurʾān: Praying behind the Lisper,’ Islamic Law and Society, 23 (2016), pp. 23-51
-
‘The Grammatical Blunders of Qurʾān Reciters: Zallat al-qāriʾ by Abū Ḥafṣ al-Nasafī (d. 537/1142),’ Journal of Abbasid Studies 2 (2015): 1-37.
-
'Revisiting Ibn Mujāhid’s Position on the Seven Canonical Readings: Ibn ʿĀmir’s Problematic Reading of kun fa-yakūna”,’ Journal of Qur’anic Studies 17.1 (2015): 85–113
-
'The Two-Rāwī Canon before and after ad-Dānī (d. 444/1052–3): The Role of Abū ṭ-Ṭayyib Ibn Ghalbūn (d. 389/998) and the Qayrawān/Andalus School in Creating the Two-Rāwī Canon,’ Oriens 41 (2013): 41–75.
-
‘al-Muhalhil in the historical akhbār and folkloric sīrah,’ Journal of Arabic Literature 40 (2009): 241-272.
這部分翻譯自在線文章「Shady H. Nasser」

